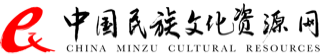彝医发展
彝族聚居于我国西南地区,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等省区,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支系和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。同中华各兄弟民族一样,彝族人民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,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及疾病的斗争实践过程中,创造和积累了具有彝族特色的传统医药学。
彝族医药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,彝族先民生活于森林中,对植物有最直观和认识和经验积累,在母系时期的凉山彝族地区,常常以一种植物来代称某个部落或部族,甚至有的山岭等地名也来自植物名称,如“达罗波”、“达日波”、“舒祖波”等,其意为黑色的阙山草、阙山草及生长杉树的山。这种命名习惯,从母系社会一直延续到今天,至今凉山地区仍不乏以植物命名的地方,如勒乌(大黄),尔吾(土香薷)等地名。彝族先民在生活过程中,对植物知识有了进一步的积累,不断地发现一些有毒的植物。“中毒”和“毒草”的概念是在彝族祖先采集野生植物和放牧生活中,出现了畜牧和人中毒的现象,加上口尝身试积累而产生的。彝族先民对毒草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,并将之记录下来,以指明毒草生长的地方以及毒性的部位,示于后人,如他们认为乌头属植物“毒藏在根上,花开在头上”。
从公元初年到南诏彝族奴隶制建立之前(公元八世纪以前),彝族经历了奴隶社会前期,在此时期,彝族医药与汉族医药有了互相交流。彝医使用的一些有效药物也被汉医使用,并且收录进汉族医书中,如《名医别录》中收载了一些彝族地区药物,在《华阳国志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汉书》、《续汉书》、《博物志》等书中,也记载了一些彝族使用的药物,这些都说明了该时期彝汉医药的交流,不仅促进了彝族医药的发展,同时也丰富了华夏传统医药宝库。
彝族有本民族文字,彝族史诗中就有很多医药知识,现在所能收集到的最早的彝族医药文献始于明代,在此之前彝族历代对药物的记载非常零星和分散。自明代开始出现了多部收载彝族医药有关的著作和文献,如《滇南本草》、《双柏彝医书》等。明清以来,彝族医药的应用更加广泛。彝著《献药经》中记载:“植物皆配药,蔬菜皆配药”。《献药经》是彝族经文《作祭经》中有关人之生老病死的一个部分,是专用于彝族成人死亡时诵念的一种古典经文,包含着丰富的医药知识,反映了彝族古代医学思想,叙述了人从父母结合、胎儿发育、幼儿成人,一直到年老病故,其中包括许多医学思想,疾病名称,药物采集、加工、炮制、煎煮、配合等内容,含有大量植物药和动物药的疗效功用等珍贵资料。此书不仅记录了彝族的古老风俗,也提供了古代彝族的医药资料。书中明确记载了草果、红果、生姜、胡椒、老母猪赶伴草等药用植物的主治功效,认为凡药用的植物、动物、家畜、五谷等,都可用来相互配合使用。《献药经》还体现了彝族医药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,就是药物相互配合使用以提高疗效,认为只要是对病情有效的药物都可以进行配合,药物配合应用十分广泛,充分说明了此时期彝族医药已从单方向复方迈进了一步。
彝族人民长期生活在山林地带,除了应用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之外,也发现和应用一些矿物药。尽管彝族医药中使用的矿物药较少,但其起源很早,彝族很早就开始应用一些相对容易获取的天然矿物药,如天然硫黄、天然火硝、盐块、金屑、银屑、扁青、青碧、盐、琥珀等,并且一直沿用至今。
近代,彝汉医药交流日益增多,彝医吸收汉族医学的内容,逐渐摆脱过去用药简单,仅凭经验的传统格局,彝族医药有了长足发展,近年来相继出版《中国彝族医学基础理论》、《中国彝族药学》、《中国彝医方剂学》、《彝族医药荟萃》、《云南彝医药》、《彝药本草》等彝族医药专著,彝药现代研究与开发蓬勃发展,彝族医药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